我的一生都是在苦难中成长,在我呱呱坠地时,一九二七年,北伐革命的战争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,在漫天烽火中,一家人过著颠沛流离的生活,几乎在内战中结束小命;十岁那年,中日战争的爆发,我们又开始四处逃亡。十二岁出家后,我到各个名蓝古刹参学,跑遍京沪一带的丛林。二十三岁时,国共相抗,神州板荡,我从栖霞来到宜兴,又从宜兴到南京,辗转播迁台湾,此后,再度过一段浪迹天涯的日子。长途跋涉,经常移徙的体验,使我在弱冠之龄就感悟到:「世间上什么都是我的,什么也都不是我的!」所以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,都能随遇而安,随喜而作,因为普天之下,只要你容他,他就是你的;你不容他,他当然就不是你的。
不经意回首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我从台湾北部走到台湾南部,一路行来竟是丽日风雨兼而有之,对于宇宙万象的体验,我依然觉得:「如果用入世的眼光来看,什么都是我的,其实什么都不是我的;如果用出世的态度来看,什么都不是我的,其实什么都是我的。」太执著于拥有的人生固然辛苦,太放弃、太空无的人生也未免过于晦涩,最好是能将两者调和,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,以享用而不占有的观点来奉献社会,才能为自己、为大众铺设一条康庄的人生大道。
因此,当有青年向我乞求剃度出家时,我总是先问对方:「佛光山是谁的?」如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:「师父!如果我在佛光山出家,佛光山当然是我的!」这句话就算通过我初步的考核了。因为唯有觉得常住是我们自己的,每个人才肯奉献身心,安住求道,寺务才能日益兴隆;唯有觉得师兄弟是自己的,才肯包容他们的缺点,成就他们的长处,大家才能和乐相处。
每次我在佛光山巡视散步,当我驻足在西来泉畔,聆听淙淙溪声,彷佛看到早年洪水爆发时,师徒们合力以身挡水的壮观场面;走到大雄宝殿前的成佛大道上,又好像见到当年大家在烈日雨水下,拿著铁尺,就著未乾的水泥地刻画纹路的辛苦情景。
三十年来,因为我们将佛光山看成是自己的,所以才能众志成城,将蓁莽未启的荒山开辟成庄严殊胜的净土。唯有觉得一切都是我的,才能产生源源不绝的动力。希望我的徒众都能时时把「佛光山是谁的」当作话头,努力参究。
佛光山既然是我的,当然也属于大众每一个「我」的,因此从开山以来,所有设施都是随顺信徒所需而兴建,一切重大计画都是经过大家开会来决定,乃至典章制度里的每一则条文,也莫不是在公开的场合中通过公布。一九八五年,我依章程退位,将住持之职交由第二代接棒,许多信徒前来哭跪请留,都无法挽回我坚决的意向。经云:「依法不依人。」大家是否都能在平等的「法」中,看到佛教的本质与未来?
是的,佛教主张「法不孤起」,所以既不执著一法一人,也不舍弃一法一人,正因为佛教的本质如此,因此才能结合众缘,不断突破,创造远大的未来。我虽然已经退位,不是住持,但我还是徒众口中的师父,还是佛光山的一分子,因为师父是永远不会退位的。所以当常住需要我时,我还是义不容辞的提出建言;当弟子请求我时,我也愿意为大众排难解纷。
对于佛教事业,我也是本著这种不执不舍的精神,戮力以赴。出家数十年来,从撰写文章到办小型报纸,从建设道场到创兴学校,从街头巷尾布教到国家殿堂讲经,从数十人小型的座谈会到几万人大规模的活动……,凡是有益于振兴佛教的工作,无论是不是我来主办,只要有人邀请,我一定乐意前往,共襄盛举。
不管那一家佛学院找我教书,我都觉得学生是自己的,所以倾囊相授,毫不私藏;当他寺邀请我主持僧伽讲习会时,我也未曾将学员看成是外人,所以一律有教无类,行无量法施。随从的弟子说:「师父竟然把全部的秘笈交给别人了!」记得《六祖坛经》中,曾记载一位同参道友质问惠能大师:「上座还有密意否?」惠能大师回答说:「密意尽在汝边。」对方闻言大悟,惭愧作礼而去。所谓「事无不可对人言」,真理遍满法界虚空,毫无密意可言,只看我们肯不肯留心观察罢了。
从大陆到台湾,我每到一地,都把一切看成是自己的,哪里可以学习,我就前往那里请益求教,那里需要帮忙,我也尽心尽力地为其服务,所以丛林四十八单职事,我样样知道。在参禅念佛方面,我也曾有万物俱泯的境界;对于宗下、教下、律下的义理仪规,我固然了然于心;对于各个教派道场的历史渊源,我也是如数家珍。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个人的,所以只要有机会,我也很乐意与大家分享。
至于友寺的制度,我向来采取尊重原则,然而一旦求教于我,我一定帮忙解决,因此朝元寺兴建朝山会馆时,我亲赴指导规画;灵岩山寺打水陆,我也派弟子前往参加;其它如东净寺、双林寺的法会活动,我都督促徒众热心支持。弟子偶尔向我诉苦,自己道场的活动都已经忙不过来了,还要插手管别人的事。我最不高兴听到这些话,于是反声相诘:「什么是别人的事?」
佛陀等视一切众生如佛子罗睺罗,我们以佛陀为本师,自应追随效法。近百年来,佛教之所以衰败,不就是因为派系之间妄自分别,贻误后人吗?实际上,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上,拈起一毛,万法皆随之而生,所以,自他不二,人我一如,别人的事其实就是自己的事,如果我们能常作如是想,又哪里会有忙闲、好恶的分别呢?万法一如,众缘一体,这是佛陀的本怀啊!
出家以来,曾经遇过一些人前来问难,他们指著儒家所说「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」、「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始也」等文字,驳斥出家披剃之非,显然是以辞害义,不明就里所造成的偏差意识。记得一九六二年,兰阳救济院因经费不足,即将关门,我当时虽然自己也是捉襟见肘,但基于一份恻隐之心,伸出援手,应允接管,这一来不知解决了多少无依老人的食宿问题。我深深感到:假如把天下的老人都看成父母,未尝不好。是自己的父母,未必像自己的父母;不是自己的父母,有时比自己的父母更好。所以是自己的,有时不是自己的;不是自己的,有时反倒是自己的。
早年,一些人经常将一些路上拾来,不知姓名住址的小孩送来佛光山,我盖了一座育幼院收容他们,后来在报户口的时候,户政机关不肯接受,我见主管院务的职事深怕继承财产问题会为日后惹来麻烦,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,所以又自愿将他们归在我的户籍下,跟著我的俗姓「李」来取名字,并且送他们上学读书,使得他们不致流落街头,如今都一一长大成人,服务社会。
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将天下的父母视为自己的父母,将天下的子女视为自己的子女,什么人都可成为我们的亲人;如果没有爱心,亲人也会形同陌路。所以世间上的人可以是我们的,也可以不是我们的。我有千人以上的出家弟子,个个都比一般人家的儿女更好。我在荣民总医院开刀,作心血管绕道手术,真是有几百人排班侍候。我没有儿女,但像有更多的儿女。所以我很确定什么是我的,什么不是我的。其实只要心能包容,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,一切法界都是我们的。
我们以为身体是我们的,其实身体是四大五蕴积聚的;我们以为财富是我们的,其实财富是五家共有的;我们以为儿女是我们的,其实儿子是媳妇的,女儿是女婿的;我买的土地供他人建房屋,我建的房子供他人住,甚至于历经千生万死建立的江山朝代也都可以更换。看得破的人,什么都是我的;看不破的人,什么都不是我的。我一向提倡「以无为有」,我拥有「空」,看起来什么都没有,其实空即是色,色即是空,虚空中不是一切万象俱全吗?
一九四九年,我从大陆到台湾来,连衣履都不全,看起来什么都没有,到今天我感到世界都是我的。有人说可惜我出家了,不然就像王永庆一样。其实王永庆被誉为经营之神,在财富上如何能跟他相比?但可以说他拥有实质财富,如六轻、南亚、台塑等,而我所拥有者,则是无形无相的三千大千世界。
披剃五十年来,我对母亲的孝心恒久不变,对其它亲友也总是量力接济,只是我有自己的原则与方法。有的徒众看我对于苦难者的求助慷慨解囊,对于亲人的需索反而思前顾后,心中百思不解,于是前来问我,言语中带有不平之慨。我回答他们:「因为我不认为亲人是我的,更不觉得苦难者不是我的。」
当我们行走街头,目睹贫富贵贱、少壮老弱,和我们擦身而过;当我们踏青野外,但见走兽爬虫、飞鸢游鱼,与我们相视对看,焉知何者不是自己过去世里的父母亲眷?究竟谁是我的?谁又不是我的呢?所以,该给的,我万金不惜;不该花的,我一毛不拔。唯有等视一切众生,拔苦与乐,才是真正的回报深恩,因此我发愿生生世世来此人间,学佛行道,度脱有情。
曾经有人和我说:「为什么对那么顽劣的徒弟,还要煞费心机?」我想,就是因为他冥顽不灵,我才要多花心思,将他导向正道。子女再不好,几曾看过为人父母者嫌恶舍弃呢?树上的叶子掉落下来,因为不是「我的」,所以一点也不感到疼惜;身上的皮肉受伤化脓,因为是「我的」,所以每天用心敷药包扎。如果我们能将众生视为自己的眼耳鼻舌、手脚四肢,就会珍惜每一个因缘,心甘情愿地为对方付出一切。
前些日子,一名信徒恭敬地捧著一个破旧的红包袋给我,腼腆地说道:「它已经在我口袋里放了三年,每次您都来去匆匆,没法子送给您,今天总算让我遇到了。」对于信徒的厚爱,我真是感激不尽,但是我的确打从心里将信徒看成是整个佛教的,从未视为个人所有,因此每次主持皈依典礼完毕,我总是赶快离开,恐怕沿途受人跪拜;每回大座讲经下台,我也是潇洒而去,不带走一个掌声。但是只要大家有困难找我,我一定为他们解决。
经云:「所有众生,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,而实无有一众生得灭度者。」又说:「众生众生者,即非众生,是名众生。」惟有保持一颗无所得心度众利生,我们才算是真正拥有了一切的众生。
所谓「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」,我虽然「出家」,但并没有「出国」,因此我从不放弃国民应尽的义务,政府举行选举的时候,我去投票;中央邀请我在全国大会上出席说话的时候,我挺身建言;甚至我作不请之友,为纾解两岸紧张关系而穿针引线,为拓展国民外交而周游海外。但是我不逢迎达官显要,也不攀缘权亲贵戚,因为国家社稷是我的,所以我必须尽忠职守,而功名富贵是过眼云烟,并不是我的,何必汲汲追求。
一九四九年,我来到台湾以后,本省人一直喊我是「大陆来的和尚」;一九八九年,我首次返回一别四十载的家乡,行至大陆各地,大家却都说我是「台湾来的和尚」,一时之间,我突然对于自己应该隶属哪里,感到模糊起来。后来我走访各国弘法,才发觉自己每到一地,都将当地视为是我的家乡,所以我睡得安稳,吃得自在。
白人的胡睛碧眼,固然清新大方,黑人的黝肤卷发,看起来也美丽高贵,欧洲的古堡令人发思古幽情,非洲的森林也颇具原始风味。只要我有一颗泛爱大众的慈悲心,又何必自我设限,将自己局促于某一个国度里呢?于是我立意要做一个「地球人」,把自己奉献给全世界的众生。因此,我在海外各国建设数十家道场,成立世界性的「国际佛光会」,希望凡是与我一样有国际观的同好,都一起来拥抱地球,为世界的和平安乐携手合作。
我们的心胸有多宽广,就能包容多少事物,所以身体固然是我的,国土、众生、地球也都是我的,甚至只要我们具足慈心悲愿,立意直下承担,整个宇宙都是我的,然而一但放下万缘,就是自己身上的一毫一发,乃至坐拥三千大千世界恒沙七宝,也都不是我的。所以应该有无量喜舍,普施回向的度量。
过去秦人遗失一把宝剑,不但不懊恼,反而说道:「天下人失之,天下人得之。」这么一转念,不但宝剑没有失去,而且还拥有了全天下,何其乐哉!失去与拥有,包容与喜舍,其实是一体的两面,惟有将两面结合起来,我们才是真正地提起了全部。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生活,若能同时具备「什么都是我的」胸怀,与「什么都不是我的」雅量,才能如行云一般舒卷自在,像流水一样任运而行。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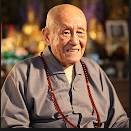 梦参老和尚
梦参老和尚 玄奘大师
玄奘大师 大安法师
大安法师 如瑞法师
如瑞法师 弘一大师
弘一大师 省庵大师
省庵大师 界诠法师
界诠法师 妙莲老和尚
妙莲老和尚 圣严法师
圣严法师 其他法师
其他法师 憨山大师
憨山大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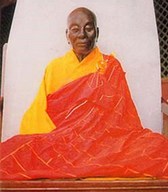 六祖慧能
六祖慧能 净慧法师
净慧法师 绍云老和尚
绍云老和尚 太虚大师
太虚大师 净界法师
净界法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