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在旅途,往往要考虑:今夜宿何处?
大多数人会把驻足点设想在尚未到达的前方某一处,而极少能于当下止步,安心即住。
稍有身份的,或较有钱的,都想赶到城里住宾馆。因为住宿条件若不够理想,他们是难以安睡的。
还有些人,要求住宿处有酒吧、歌舞厅、桑拿浴等,他们注重的是娱乐、消遣、刺激,而不在于住宿本身了。
而开着豪华小车出行的人,只要有可能,则会尽量赶回家里哪怕是行到天亮! 因为家里豪华、富有, 出门在外便放心不下、安身不得。
也有人,家境很一般,本无需牵挂,也并非要节省住宿费,但仍尽可能赶回家住, 只是缘于“金窝银窝, 不如自己狗窝”的习惯心理所驱使。
再有一种人, 出门为谋生计,对住宿也就无法讲究。走累了,或乘车停靠了,随便找个旅店,倒头就睡,一觉到天亮。他们虽不能把异地他乡当家,但也算能够 随遇而安。
看来,“家”已成为世俗人旅途的后方乃至归宿。家, 既给旅人以信心和慰籍,又往往成为旅人难以割舍的包袱。人们既无法带走它,又时时在心中装着它。心中老是牵挂着家的人,其旅行是很难获得愉快、自在的。
当然, 也有一类无“家”观念的人——无家可归的浪子,他们东游西荡,倒头可睡,这并非出于潇洒自在,而是因为人生旅途毫无方向,所以只是形尸走肉般地醉生梦死罢了。他们糊涂入睡,醒来之后大抵如宋人柳永在《雨霖铃》中描绘的那样: “今宵酒醒何处?杨柳岸、晓风残月”。
作家戴厚英说过: “家庭不是后方,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处驿站”!是的,漫漫人生恰如长途跋涉,旅行的目的不是要去寻找一个家,人生的终点更不是要回归到形而上的“家”,否则,就不必从家出发去旅行了。
红尘中的人们都懂得“饥来吃饭,困来即眠”的生活规律,但在人生旅途中本该安歇时又总是因为有太多的牵挂和无奈,狂心不息而不能安住。正如唐代大珠禅师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所说: “他吃饭时不肯吃饭,百般思索;睡时不肯睡,千般计较”。如此,错过眼前,放弃当下,一路疲于奔命,其心不安,其身疲惫。这样的人生旅途,哪里还能让人感受到恬静和美丽、圆满和自在!
然而,却有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“旅人”一一云游、行脚的僧人,他们头戴一竹笠, 身背一行囊, 出行不虑阴、晴、雨、雪,不计春、夏、秋、冬,既不需美食锦衣,更不愁夜宿何处,行止随心,一切随缘,可谓是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。旅行中,若逢天黑了,路边小店、茅棚、山洞均可栖身,甚至在路边、树下即可坐卧,天当房、地作床……正如清末高僧仁智禅师所说: “一钵千家饭,孤身万里游。前途何处在?念佛度春秋”。
这些行脚僧之所以能安心即住、无虑 无畏,一者,其身不怀金银财宝,便无他人图财害命之虞; 二者, 明白人生本苦, 住宿的优劣也就无所谓:三者, 出家修行 本为寻求解脱,心中了无挂碍, 自然不会对一身躯壳百般爱惜、千般呵护了; 四者,更无一个“家”可挂念,虽然天下丛林任僧住,但既然不贪恋,也就无所谓有 固定的家,也就能四海为家了。漫漫人生路,他们不迷茫, 因为心中早已认准了一 个明确的方向; 处处有艰难, 他们不畏惧, 因为修行本身就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!他们的内心是充实而沉稳的,他们并不等待未来,也不沉缅过去,而是专 注于对当下的把握,安心于当下, 内心充实、平和,举止安祥、从容,时时保持一颗平常心, 以“平常心是道”的态度,踏踏实实去走好人生旅程中的每一段路。
从古到今,世俗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些“云水僧人”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,视僧人的行脚为极苦。而贵为帝王的宋仁宗却对以苦为乐的僧人生起羡慕、赞叹之情,欣然御题《赞僧赋》,偈曰:
空王佛弟子,如来亲眷属。
身穿百衲衣,口吃千钟粟。
夜坐无畏床,朝睹弥陀佛。
腾若得如此,千足与万足。
那么, 还将在人生旅途中远行的人们,何不学学那些行脚的僧人,果敢地斩断对后方的种种牵挂、顾虑,放弃对远方的虚无飘渺的幻想,而专注于眼前,把握好当下,不必行旅匆匆,但求步履从容,在人生旅途的每一处驿站,安心即住,涵养自性的宁静, 感悟生命的充实……如此,既可以领略当下的“本地风光”,更可以享受人生的任运自在!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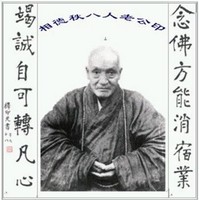







 莲池大师
莲池大师 其他法师
其他法师 憨山大师
憨山大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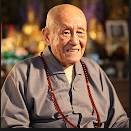 梦参老和尚
梦参老和尚 智者大师
智者大师 印光大师
印光大师 玄奘大师
玄奘大师 广钦老和尚
广钦老和尚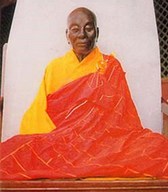 六祖慧能
六祖慧能 大安法师
大安法师 如瑞法师
如瑞法师 虚云老和尚
虚云老和尚 慧律法师
慧律法师 净慧法师
净慧法师 圆瑛法师
圆瑛法师 弘一大师
弘一大师